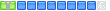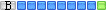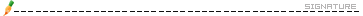妻走了,而且是永远地走了。她走的是那样的突然,又是那样的匆忙,仅仅才有六天的时光。噩梦中醒来的我的只有迷茫、怅惘、思念和神伤……。
不论是在120急救车上,还是守候在NCU病室的门旁,我都抱着希望。因为与我相濡以沫二十八年的妻,一向乐观、一向坚强,决不会离开我独自走向那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她一定能好转、一定能康复、一定能回家,哪怕是病卧在床。然而,蛛网膜下腔的二次出血,使医生束手无策陷入无力回天的彷徨。2004年7月8日16时25分,妻还是走了,一声不响的走了,走的是那样的安祥,似乎熟睡在梦乡。我的泪在流淌,心被撕伤,我恨死了自己,为什么在这生死离别的时候,才刚刚解读开“夫妻”这只有两个字的文章。妻呀!我对不起你呀!二十八年来,你总是伺候着我、迁让着我、疼爱着我,而我的心中却只有我,还时常地乱发脾气把你的心伤。你走了,今后我来和谁讲述烦恼、诉说衷肠……。
妻走了,家中失去了大梁,只剩下年迈的老人、上学的女儿和我各自独卧宽敞明亮的房。看着妻用过的东西和穿过的衣裳、我的心是那样的窄、暗、空、凉。窄的容不下自己、暗的不见光芒、空的透不过气来、凉的肺腑发慌。脑海里只有妻的音容笑貌和二十八年的回忆遐想……。
妻朴实无华、内涵高尚。妻叫李玉芹,我们相识在1976年那场灾难的前的时光。那时,我们双双下乡,她在陡河水库的西岸,我在开平南部的聂各庄。不过她是真正的下乡青年,而我却是“反革命狗崽子”饱受歧视、百般凄凉。能有谁和我谈对象?能有谁作我这样人的新娘?就在这个时候,妻悄悄地来到我的身旁。她默默地听我诉说父母、家庭的政治、经济状况,眼睛里流露出同情、信任的光芒。尤其是在震灾发生后,妻背负着父母、姊妹、兄弟六人罹难的忧伤,忍受着他人质疑、鄙视的目光,毅然走进我那破烂、穷困、低矮、潮湿的简易房。妻的到来、给自卑、孤独的我增添了对未来的向往和生活的力量。妻后来回城工作时,为了避免我的胡思乱想,不管雨雪风霜、道远路长,几年如一日往返于城乡,总是把温暖送到我的心上、送到我的身旁。
妻乐观大度、贤惠善良。我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疆场,因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文革”中被迫害身亡。母亲为了我,改嫁来到继父的家乡,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却一直戴在头上,再加上疾病的折磨,年仅四十四岁就读完了她人生这篇苦涩的文章,家庭的版图一下子变得苍茫荒凉。妻来了,绿化了我们父子生活的沙漠,带来了鸟语花香。春末,她拆洗好冬装;盛夏,她打好了菜卤、做好凉汤;秋始,她将织好的毛衣送到我们父子、女儿的身旁;寒冬,她总是等我回来炒菜、再把酒杯放在桌上。她反对我喝酒过量,但还是将择好的鱼肉、剥好的皮皮虾放到我的碗里、筷旁,嘴里还叨咕着“喝、喝……!那酒准是忒香。”她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成快的布料都是给我做成西装,让我上班、开会、主持婚礼时仪表堂堂。而她自己的衣料却是选在布头市场,东挑一块、西找一块、裁裁缝缝穿在她自己的身上。
妻勤劳忠厚、正直倔强。妻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兄妹八人、全家十口的生活,全部依赖岳父一人工作在启新水泥厂。生活的拮据、家庭的困难,使妻小学都没有读完就奔波于渣滓场上,成了一个拾煤渣脏姑娘。冬天的严寒扭曲了她的双手,成了她走完五十七年人生的残伤。我曾目睹她下乡生活的一天时光,让人感叹、至今难忘。天还没亮就上了渡船,赶赴水库的东边一方,一天挥汗如雨的劳作,中午却只能顶着烈日啃着带去的干粮。回到家中已是星月辉煌,妻还得守在灶旁。直到她回城上班时,如正值农忙,回家也要帮我薅苗、割麦、掐高粱……,从没有因苦和累而嘟嘟囔囔。父亲的平反、昭雪使我得以回城工作,也曾一度在企业把领导担当,但妻却从不张扬,她没打过电话、没进过单位、更谈不到要求单位办什么事、帮什么忙。就连她走了,都不知道我工作过的机关座落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我的妻,我一直未能了解的妻、我一直未能珍爱的妻。妻走了,我才感悟到她情操的高尚、挚爱的光芒。望着妻的遗像,我哭泣、我忏悔、我烦闷、我感伤。我能否用这迟到的爱来恳请妻的原谅、来弥补我的心殇。如果真的有来世,我一定加倍珍惜我与妻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大好时光,决不再作忏悔的文章。玉芹,我好想你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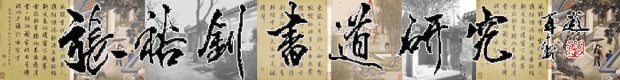




 谢谢我的朋友们
谢谢我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