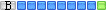看不到!



张裕钊与汉镜铭
■熊寿昌
张裕钊(1823-1894),湖北鄂州长岭龙塘村人,为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古文家和书法家。他一生漂泊在外,先后在武昌、南京、襄阳等地书院任山长(院长),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和书法作品,培养出一大批有才华的学生。一般人只知道张裕钊的诗文书法在社会上有影响,其实,张裕钊还是一位钟情于铜镜等文物古玩的人。复旦大学中文系老教授柳曾符先生在其《我终于弄明白了张裕钊手中的汉玉》(载《张裕钊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选》)一文中谈到,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拜访著名书法家王遽常先生时,据王先生讲,张裕钊当年在南京凤池书院时,每每外出,坐在轿子里,手上总要拿一根汉玉,不断在手中摆弄。是张裕钊把玩玉器吗?也许有这种因素,但是,张裕钊真正的目的是在把玩汉玉的同时,把汉玉当作一支笔来揣摩写字时的换笔方法。
张裕钊确是一位既酷爱文学书法,又珍视文物古迹的学者。据张裕钊的《濂亭文集》所载,同治七年(1868年),张裕钊在南京时,“江宁承乱后残剥,一天有闲,欲求故家文物、先贤遗迹。”他与著名金石学家吴大瀓(1835年-1902年)等人过从甚密,常结伴相游。光绪十年(1884年),张裕钊应李鸿章之聘任保定莲池书院主讲的一年之后,河北武强县的贺涛(?-1912年)来拜张裕钊为师,执弟子礼,成为张裕钊的入室门人。贺涛,字松坡,是张裕钊弟子中颇有成就者,为继张裕钊之后古文桐城派的中坚。特别是他的书法,受张裕钊的熏陶,得益颇多。他曾记录下张裕钊对自己书艺的总结――“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笔轻,入墨涩;发锋远,收锋急。”两年后,贺涛便考中了进士,后官至刑部主事。
贺涛的成长与张裕钊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从张裕钊写给贺涛的《汉镜铭》就能看出这点来。《汉镜铭》正文曰“许氏作镜自有纪,青龙白虎居左右;圣人周公鲁孔子,仕吏高迁车生耳;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落款为“松坡仁弟属,廉卿张裕钊。”汉代铜镜是中国古代铜镜中的精品,它图案精美,铭文丰富,思想性强,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从宋代开始到今天,一直被收藏家看好。汉镜上的铭文大多在铜镜的边缘部分,环绕一周。张裕钊写给贺涛的这幅作品的文字系直接从铜镜上抄录而来,它是典型的汉镜铭文格式,鄂州出土的铜镜中很多就有类似的铭文句式。从这幅作品的文字内容可知,之所以选定并书写该镜铭,主要也是通过它来勉励贺涛,因为铜镜本身就有“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哲学内涵,加上铭文所反映出的思想内容,所以,张裕钊选定这面汉镜的铭文书写后送给贺涛是再贴切不过了,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裕钊对后生的关爱与鼓励,恐怕也是张裕钊委婉地表达他爱才惜才的一种方式。
张裕钊的《汉镜铭》,后被人刻石相刊,该刻石后又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镜铭之于刻石,可谓是铜镜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延伸。这面汉镜是出土于南京、保定亦或鄂州?收藏者是张裕钊、贺涛还是别人?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庆幸的是,留下了张裕钊的这一刻石作品,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铜镜、研究张体书法的宝贵资料。


熊寿昌文所附《张裕钊汉镜铭》见11楼的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