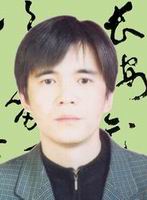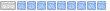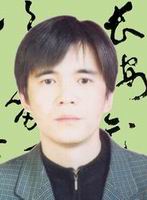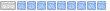第 2 楼

张裕钊的书法,确实别立一家门户,不同于有清一代的诸家。用笔苍劲,峻如刀削,锋敛而见芒;结体修瘦,严谨有制,外方而内圆,然则,取法于何处呢?
有人说他“取法六朝而面目全非……”,不错,这样意态风格的字,古人所无,但精心细窥,确有绪脉可寻。说他出于《张猛龙》,诚然有之,如出捺时,收而不放,轻不著力,颇足提神。而于折、钩处却着力刻凿。说他有《崔敬邑》意态,诚然有之,如“博睦.的“睦”字,“京夏”的“夏”字,确实形神相肖。说他结构出于《吊比干》,诚然有之,如“原而”、“见”、“勇”等字,取势成体都有似处。康殷先生说他出于《张贵男》,当然又一新见,结体之拙巧果然相同。凡此种种,可以看出他确实遨游于魏碑这座宝库之中,俯仰之间裁取不少,诚然可以说他是“善于熔铸”,而集其成,自为机杼的一“家”。
然而,为什么康有为又说他“专学六朝书,而所成乃近率更、诚悬”呢?是“取法乎上仅得于中”等而下之所至吗?对此,我有一点很不成熟的看法,胃昧地说一说: 我觉得,张裕钊先生并不见得“专学六期’,这个专字值得分析,因为从六朝直接到张裕钊,从结字成体上看,缺乏必要的过度。固然《张猛龙》是横扁而纵狭参差互见,而廉卿先生则一意修狭,瘦长取势,正与柳公权的《神策军》尽力伸长一致,尤其与欧阳询诸贴相同。《九成宫酸泉铭》的雄秀相融,对应成趣的立意,虽然他未作过多的寻求,但《皇甫诞》的峻利秀拔,《度恭公》的剥蚀古朴,《化度寺》的规格严正.却比比皆是,绝非偶然而成。这种结果,如果没有着意的追求,是没有条件达到的。所以我觉得张裕钊先生并没有舍弃了对唐碑的摩拟。甚至于可以说他不是从魏而至唐,而是自唐上溯于魏。看看张裕钊先生的小楷《千字文》,距自唐至清的体制相去几何?
对于张裕钊先生的书法,我觉得:结字他以唐为主,加之以北碑的神采,人笔颇有篆法,行笔则取势于北魏,藏头护尾,中正不倚,折笔取法于汉隶,撇捺敛锋,出钩迥锋,蓄而不使芒颖外显,但是精神爽利,法度俨然。
要着重一提的是:张裕钊先生选笔则用硬毫,可以笔秃无锋,但不喜其软。这从他所书日课“诗经,等字的墨迹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在薄纸易透,迎光从背面看去,或从纸面平眼望去,松捆泛于纸面,浓淡回笔都可历历如见。特别在蜡笺上看,墨不人纸,毫锋只能在纸面上滑动不刻,更易看出毛笔的活动趋向,可以看出张裕钊先生之所以如此,恐泊意在追摩古人刻石之刀痕,石质剥蚀后的自然悄趣。对于这一点,评者好恶皆有,我们现在都不作论,我们所注意的是张先生的趣旨所在,慕求所之,这对我们的学书极有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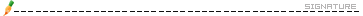
当书被借时,总要喋喋不休地千叮咛万嘱咐,深怕自己心爱的“孩子”在外会遭千般苦万般难。当一本书被弄得伤痕累累遍体鳞伤归还时,就像自己的孩子寄宿在他人家被他家的孩子欺负,嘴上虽然说不要紧,心里却心疼得要命。我就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