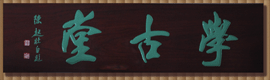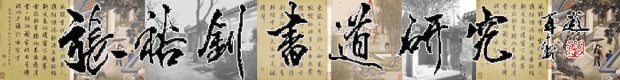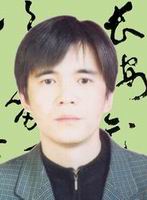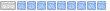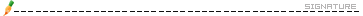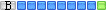得失参半——张裕钊的生硬
| |||
陈振濂 著 张裕钊本来是不甚引人注目的,但我们读了康有为的“千年以来无与比”“尤为书法中兴矣”的评语深为纳闷,云吴昌硕可;云赵之谦、沈寐叟亦差可,云张裕钊而高标如此,何也?于是,本不被人注意的张裕钊忽然成了众所注目的对象。 但结果还是令人失望:按书法家的眼光去看,张裕钊不失为“一家之言”。若以他为千年以来领风骚者,不但那些大师们心不能平;就是曾被我们批评过的郑板桥乃至上溯王文治、唐寅、陆游诸公也断然不能接受——何厚此薄彼之甚邪?批评一旦失去了公正,则批评本身的效率可想而知。故康有为之论一出。马宗霍即毫不客气地指为“过情之誉”,即使他是“南海圣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也不足忌。 倘若我们以晚清为碑学大盛并进入总结期的话,那么张裕钊除了他的逋峭生硬稍能戒除圆熟之气外,更多地倒是暴露出碑学的不利面。这就是,以柔软的毛笔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溯石刻刀斧凿痕的方折效果,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不惜在行笔时故意追求外方内圆的抖笔、斜锋、侧刷等动作;由于这种种动作违反了毛笔的基本性能,因此线条的生硬梗突感十分明显。至少它比柔顺的线条更出人意外,而比古朴浑厚的线条则少一种深沉博大的气概。 我对张裕钊持一种特殊的看法,我认为如果把张裕钊与其他书家作同等观,我们可以把从王羲之直到何绍基吴昌硕的书法比作恒常强身健体的名药,而把张裕钊看作是一种特效药。强身健体的补药,对人人皆有滋补之效,而特定的药则只能在特定环境下有效;一旦抽掉环境,则药的价值等于零。面对赵之谦徒子徒孙们的油滑轻圆的书法,张裕钊是一剂特效药;但若我们发现历史上并投有太多的赵之谦风气时,张裕钊的生硬则失去了光泽。后人若听信康有为的“过情之誉”,亦步亦趋地学他,那是要大呼上当的。至于什么“千年以来一人”之说,更是纯粹的扯淡。 张裕钊书风在日本倒颇有些影响,其原因大约是伴随着北碑风的席卷东瀛,以他的生硬可以为圆熟纤弱的假名书法多提供一些启示吧?但尽管如此,在众多的日本崇拜者的书作中,我们仍可一窥种种更变本加厉的突兀与生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