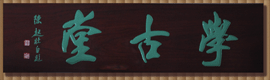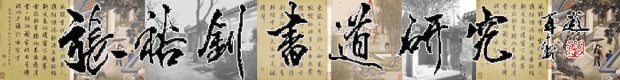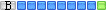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春风吹桃李 丹心育英才
——忆我的恩
田雨潇
转眼之间我的恩
先生是原来的师范学校毕业,在学校期间酷爱书画,受到当时的美术老
先生身上有一种精神,那便是认真,做什么像什么。早年他在沧州剧团里做美工,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美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背景创作活动,这件优秀的作品成为经典之作,里面有很多像他这样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的奉献。后来在沧州师范学校里教美术,他就是一个优秀的美术老师和书画家。到现在我还收藏着他的几幅当年的画作,真的是笔墨纯熟老到,他很善于把书法的用笔体现到画作里面,其实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很简单。后来随着师范学校对书法的重视,先生成了一名专职的书法老师,此后他便一心一意做好书法教学工作,他很少再以画家身份示人,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先生会画画。当年的书法课就是在先生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得到充分发展的。由于他对当时的书法教学进行了大胆地改革,使得当时学校里学生练字蔚然成风,培养了一大批书法特长的学生,也使书法成为当时沧州师范学校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他也成了当时学校里最优秀的教师之一。那时候他还兼着书画函授大学的课程,有的时候我陪先生一起去上课,帮他拿一些教学用具。他上课很认真,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厌其烦,因为学生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时候一个问题要反复地讲解、演示,所以学生听他的课,不管是什么层次,都会觉得很有收获。先生常以陶行知的一句话自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也是一直都在这样去做,总结先生的一生,书法教育上的贡献在沧州书法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活跃在沧州书坛的中坚力量有很多就是在那时候被他领进书法之门的。
在现代书法发展中,一直以来沧州的书法秉承清末尚碑的余绪,写碑的风气是很盛的,先生的书法立根也在碑,早年对唐楷以及清代张裕钊楷书、《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用功尤多,而晚年特别喜爱《汝南王修治古塔铭》,我见过先生临写的作品,可谓形神兼备,真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生的行书却是学帖的,尤其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及米芾、赵子昴、文徵明的经典,于张瑞图笔法也颇有所悟。这种碑帖结合因为风格的差异,要想协调统一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他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许多人们感觉是存在矛盾的几种书体却被他消化得很自然,表现在作品中没有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他的作品既有碑的刚劲,又不乏帖的洒脱。
我跟先生学书的时候,学习环境不是很好,没有练习纸就在练习粉笔字的小黑板上反复写,很多优秀的字帖也见不到,有的时候他在外面见到了就给我们借回来,让我们用双钩的形式钩下来然后再填上墨对着练习,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钩摹了很多的字帖。他教书法主张从基础入手,反对急功近利,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守旧,对于一些现代意识比较强的作品中的优秀成分积极吸收,甚至他自己也尝试现代书法创作,其中我记得有一幅《一衣带水》现代书法远赴东瀛展出并被收藏。我觉得一个好老师的关键作用是怎样去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路,这也是做老师的高明之处。
他在教学之余,阅读了大量的古代书论,这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也是一般书家所不能做到的,我想他当时还是出于对书法教学的考虑。他对书法史论的深入了解不但丰富了自己的教学,使得原本枯燥的练习通过他的讲解变得有趣味,也使他自己从教学中得到很大的收益,所谓教学相长,表现在书法的创作上,就是他对笔法的讲究从而形成线条丰富的表现力。
早年先生因为教学工作需要,涉猎太多,真、草、隶、篆,甚至篆刻,都能拿得起,以至于对自己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先生晚年的时候我和他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自己也颇多感慨。不过他退休以后有了时间和精力,以极大的勇气重新调整状态,对于自己努力方向有了新的认识,很明显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大家有目共睹,这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
先生得到大家的尊重的原因还在于他对工作的任劳任怨,有的时候本来不是分内的工作,不管是谁都有求必应,只要是交给他的事大家都会很放心,肯定能做得大家满意。不过他也因此要做比别人多很多的工作,而且从来不计报酬,现在想起来像先生这样的人真的是不多。不光是在学校里的事,对社会上的事也是一样,记得有一年先生为当时的沧州卫校书写校训,那时候的制作技术还不很先进,都是要多大字就得写多大字,先生为写那些字真是费了不少功夫,最后卫校的领导很满意,非要给先生一些报酬,可是先生坚决不收,最后还是让我给送了回去,后来人家觉得过意不去,又买了礼物送来,他还是让我送了回去,弄得人家也无可奈何。在他去世的那年暑假他还为一个中学义务辅导书法,当时他已经有些发病的征兆还坚持去上课,时隔不久便因病去世了。他是一个一心想着他人的人,对个人的得失从不计较,在学校期间对学生不光是学习上,而且从生活上也是非常关心,经常资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而他自己的生活一直很简朴。直到现在提起先生,人们都还是尊重有加,这是先生高尚人格的魅力体现,与眼下很多急功近利、好高骛远之徒岂止是天壤之别。
先生一派仙风道骨,为人和蔼可亲,只要你开口
虽然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让我们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不断的攀登,而作为学生也只有这样才不负先生的诲导之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