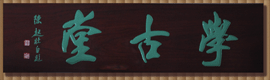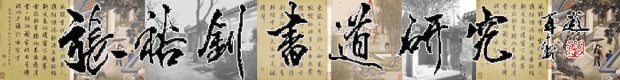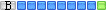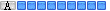张裕钊诗试论
白雉山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今鄂州市)人,出生于诗书世家。自清道光26年丙午(1846)年24岁时中举授以内阁中书后,仅任官2年便挂冠而去,终身以从事教育著述为业,成就卓著,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他曾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南京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湖北江汉书院、经心书院和襄阳鹿门书院,春风化雨,桃李争辉,为国内和海外(日本)培植了大批人材。张系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为著名的“曾门四子”之一。其古文如其师师法桐城,尤为乃师器重,曾氏曾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裕钊)吴(汝纶)二生。”又说张的古文“有安石之风,吾既爱之,又畏之。”张自己对其古文亦甚自许,曾说“自私计国朝为古文者,惟文正师吾不敢望,若以此文较之方、姚、梅诸公,未知其孰先孰后也。”张的书法更是享誉海内外,《清史稿·文苑传·张裕钊》说张“又精八法,由魏晋六朝以上窥汉隶”。康有为更称赞其书法“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陈,千年以来无与比!”以上简述可见张裕钊在教育、古文、书法上的成就,早有定评,为世所知。但张裕钊的诗作却被忽视了,不但《清史稿》和《清碑传合集》的张传中未见记载,后世的文学史和诗歌史亦未论及,近人的清诗选集也未选录,故作为诗人的张裕钊就鲜为人知,这的确是极为遗憾的。
张诗未被重视,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张的教育、古文、书法成就显赫,而诗名被其所掩,即使在其生前亦如是;二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解放后对曾国藩的评价失于偏颇,加之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盖棺定论,故对作为“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就讳莫如深,谁敢介绍其作品?更遑论对其研究宣传了;三是中国的传统诗歌在唐代已发展到了鼎盛高峰,此后每况愈下,至有清一代已成强弩之末。虽也出现过一些较有影响的诗人和神韵、性灵等流派,但毕竟难以超越前人成就。就连名噪一时的方苞和王士禛,也遭到了“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袁枚《随园诗话》)的讥评!
张裕钊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庭训极严,拜名师启蒙受教,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加之天资敏慧,勤奋好学,少年时便能出口成章,吟诗作对,颇获乡里赞誉。后虽终身致力于教育、古文和书法,但亦不废吟哦,且佳作屡见。张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他的师门好友“曾门四子”之一、曾任清末驻日本外交大臣的黎庶昌,为其编刊了《濂亭诗集》二卷问世,旋有武昌陶子麟于宣统二年庚戌刻本,后有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手稿影印本等。诗集共收录张的诗作275首,系其31岁至71岁40年间的作品。可见这并非张诗的全部,而应是一个选本。但从这个选本中,对其忧国忧民的情怀,热爱教育重视人才的态度,洁身自好的道德情操,处世待人的耿直性格和诗歌写作的娴熟技巧等,也能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