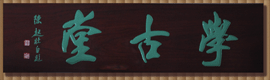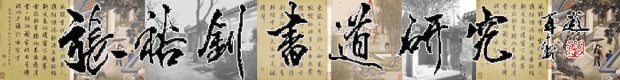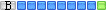但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士人,仍有放不下架子、掩饰屈辱失败的心态,于是把西方的东侵说成“自国家怀柔包荒,日月照临,天所复焘,莫不来宾。海外奇技异物、火器轮舟,诸瑰新俶诡骇怪,旷古不睹之事,并交于中国”[3](卷二),对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并无多少谴责,突出的感受是奇、异、诡、怪;同时把中国的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等等,说成是“驾远抚柔”、“交通市易”和“申结盟约”。显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到当时朝廷和官场习用语言和表达方式的影响,用自欺欺人的字眼掩饰中国的失败;另一方面在光绪十年(1884)以前的洋务运动前期阶段,所谓同(治)光(绪)中兴的假象还没有打破,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还未暴露出来,故张裕钊多少还有一些乐观和幻想。
同样,张氏此时还有一些类似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以为“天地之道,日新而不已,则文明亦日辟而莫知所穷”。他所谓文明日辟,既包括西方科技器物等文明的东来,还尤其自信中国的“周孔之教当益大被海以外,同文于冈极耳,不数十百年,可决知其必出于是者也”[4](卷一)。他相信世界人类文明会不断进步,而且这进步的原因,乃在于多种文化的交融互汇。从大方向上说,张氏的这一推测是不错的;但是他认为西方仅有物质文明、而中国的孔孟之教却具有同化世界文明的优势,这显然只是一个大胆的假定。他所说的数十百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而他的假定仍远未变成现实。
不过张裕钊较早就看出,中国要真正自强,还有许多困难,其中很重要的两点是中国人习惯的固步自封和办事敷衍。他提出,要适应“兴天地剖泮以来所未有”之“大且剧”的“世变”,必须首先破除拘守,因而批评顽固守旧人士的态度说,“当世学士大夫或乃拘守旧故,犹自鄙夷诋斥(西学),羞称其事,以谓守正不挠。呜呼,司马长卿有言,鹪明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夫薮泽,岂非其惑欤!”[5](p42-43)表明他已冲破视中国的一切为至善至美、无须改进、不可他求的传统观念,主张认真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的情况。同时,他还批评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主张讲实质求实效,称“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为虚伪。……自夷务兴,内自京师,外至沿海之地,纷纷营营,译语言文字,备火器,修轮艘,筑炮垒,历十有余年,糜耗帑金且数千万。一旦有事,责其效而茫如捕风,不实之祸至于如此”[5](p95)。这种虚应故事还表现在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不能“知彼”,而“觇国之术,柔远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应之者,乃切所施设矣。”[5](p44)所以当守旧派反对和嘲笑中国的使外人员时,他坚决支持和鼓励友人黎庶昌大胆走出国门,把掌握世界的真情作为在中国办实事的前提条件。
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夕,张裕钊已明确发现自强运动单纯讲求军事、工艺制造和经济问题,而不注重人才问题的偏颇和缺陷。他说,“今天下语边事者,皆竞言制械器、译语言文字、通商阜财、筑垒守险,一切以依仿泰西之法,筹备守御之术而无不至,而裕钊以为抑其次也。夫穷天下古今,尊主庇民,批患折难之要,一言以蔽之,曰得人而已。”张氏没有看到,自强或曰洋务运动最根本的不足,是没有触动落后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而视其失误首先在于未注意到人的问题,可说还未能切中根本,但他能看出当时重物不重人的弊病,也仍可算是卓识。
张裕钊关于“得人”的思想,可分为待人、才人、育人三个层次,可说还是较为全面的,不过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他都明显受到曾国藩父子的影响。在待人求才上,张氏认为在高位者必须象当年曾国藩那样的“名德重臣”,“既夙负知人之量,又益慕想殊,尤虚伫贤哲,早夜旁求,皇皇若不及”,才能得到人才,而且所得甚多,“九州之大,必有魁桀之士起而应之者”,“豪俊响应,焱合景从”。只要有了众多人才,就能“举议者之所云,次第而布之,一皆确然收其实效”[3](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