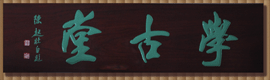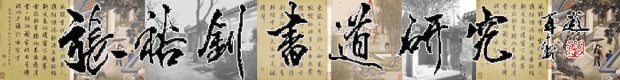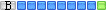怎样的人才算人才?或者说当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张氏认为,象曾纪泽这样的人才应该是人们的榜样,他说曾纪泽“博极群籍,洞晓古今治乱得失之故,益讲求时务,无所不究切。尤以疆事孔殷,所系乃绝艰大,故于彼我强弱短长之数、语言文字学术异同、舟舆器械良楛利钝、财贿生殖万货百昌赢诎盛衰,皆博考深思而心知其故。……千品万汇,宏巨密微,默识洞贯,总八极而内于寸心。故自朝野上下,无远迩、无愚智贵贱,莫不以为洞明时务未有及侍郎者也”[6](卷二)。曾纪泽是曾国藩长子,幼时接受系统传统教育;及长,受其父办洋务的影响薰陶,学习西方各种知识,又在国外八年,因而学贯中西,对中国和世界均有深切了解。1880年他40岁时,曾与沙俄谈判,改订昏庸误国的崇厚与俄国订立的条约,经反复折冲,使中国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仅有的少数几次成功的外交谈判之一。四年后中法战争爆发,他又“与法人辩争,始终不挠”,确实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干材。张裕钊以曾纪泽为当时中国亟需人才的范例,说明他的人才标准是进步的、也是讲求实际的。
在育才问题上,张裕钊曾集中论及两点。其一是批评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他说,“唯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但当时“彼所以造而成其才者失其道”,仅“学为科举之文而已”。清代的中等教学设施有两种,一是州县所设学宫,属官办性质,由教官主持;一是书院,属半官方或民间性质,由山长主持。清中叶以来,“郡县之学官权位轻而职业废,不足以鼓舞振起天下之才,于是士之有意进取者常相率聚于书院。然书院之所课其科举之业也,其主此者亦皆以科举之业进者也”。这就是说,当时的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是遭人轻视的末等官,由于位卑权微,这些人并不尽心尽责,因而州县学宫形同虚设,倒是书院能吸收一些学子。但无论是学宫还是书院,都是把教八股文、应付科举考试放在首位,学子也大多致力如此,目的是顺着科举之路,由秀才、举人、进士一级一级爬上去,好出仕做官,故“相习而靡者,苟得之弊中于人心,而莫有能拔乎其间者也”。除了教学八股制艺之外,士人所习,“或专意于考证词章之末而遗其本,或空谈性命而时不免于固陋。”到了近代,“海内兵起,人益废学,而俗日以敝。士之通知古今而可以为国家之用者,盖往往数百里而不得一人也。”[7](卷五);[5](p157-159)总之是积弊深重,人才奇缺。
其二是批评当时社会风气败坏,人人竞逐私利,而能满足其利欲的最好途径就只有作官。张氏指出,当时作为人子,能使父母高兴的是富贵利达;父母所希望于儿子的也是富贵利达;丈夫荫庇妻子的、妻子仰仗丈夫的,也仍然是富贵利达。“士大夫一沉于室家之累。身之不显则内愧妻子,而若不可为人;为子者亦若唯是可以奉承其亲,非是则危不可以为子。悉家人父子恤乎唯一官之得失为愉戚。……夫俗之日坏,而人才之所以不振,职是故而已。”[8](卷二)然而这些人表面上却道貌岸然,“其人能瞋目攘臂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而已”。所以张氏忍不住满腹忧虑地问道,“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乂安、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7](卷五)
针对当时教育制度窳败、士人不学和学无实用,且一心当官求私利的状况,张裕钊利用教学和著书等各种机会,设法挽救。他强调,“一介之士皆与有天下之责焉。将欲通知古今,讲求经世之大法,稽诸古而不悖,施之今而可行,其必自读书始矣。”然而中国之书多至汗牛充栋,读书亦“有考古之学,有知今之学,……二者固相须为用,然果孰在所缓、孰在所急”?即如考古之学一道,又有“小学”、“金石”、“史事”,“又其外杂史传记谱录之属,殆不可数。学者童而习之,白首而不能究,……其无乃鹜其近小而不急者,而转遗其大者远者欤?”话讲得很全面、很委婉,考古之学、知今之学都无遗漏,但其更重视知今之学,认为读书须注重大者远者的倾向十分明显。他曾反复强调,“古今时势异宜,锲舟求剑,胶柱鼓瑟,适足以乱天下。”尤其是当时的生存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战争,所以他虽然批评洋务运动有专讲练兵制器、购船筑垒的片面性,但也承认“自古内外强弱之势,一视兵为轻重”[9](卷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张氏力图纠正拘守故常、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的努力。
对于社会上人们争趋私利的风气,张氏也力图挽救。他认为,对此首先要引导和鼓励读书人立定崇高志向,再通过他们来影响社会,“士莫先于尚志。而风俗之转移,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今天下师儒学子,诚得一有志之士,悯俗之可恫,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由一人达之一邑,由一邑达之天下”[7](卷五),颓风未必不可挽,社会环境未必不可改变。
张裕钊因早年辞官,一直致力于著述和教学,不大直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故后之研究者多以其为有艺术性成就的文人,甚至有人批评他脱离实际。其实并不尽如此。他曾说,“道不足而强言,虽振厉其气,雕绘其词,而卒无以餍乎人人之心。深造道德而自得于其心,则凡所言而莫非至道之所寓。”[10](卷一)就是说,没有思想深度而故作大言,人们不会理睬;有了真知灼见,随时随事随意为言,都能包含有用的道理。《濂亭文集》的首篇《辨司马相如封禅文》,其实就是该书的“文眼”。在这篇文章中,张裕钊力辨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不是向汉武帝献谀,而是“正以讽武帝之封禅”,“其辞隐”而“刺讥深至”。并称司马相如等人的文章“其用意皆至深远难识,无苟为之者也。以其难识,世乃徒观其外而议之耳。”[11](卷一)同样,张氏的文章也多是意思深远而隐晦,少有激烈的言辞和直截了当的批判,但其关切社会问题的深心、其顺应时代需要而提出有关改革建议,都斑斑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