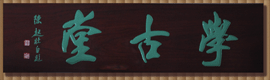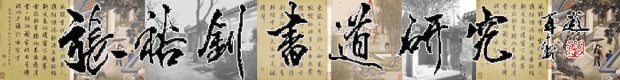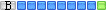但张裕钊不仅文思深沉,而且思想悲观。他深知当时颓势难挽,而自己的才学和主张亦难见用,故常借他人之酒以浇自己胸中垒块。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号鹿门)曾慕张氏之名,来保定莲池书院相访,并为其书《藏名山房文钞》求序。冈千仞与王韬亦相知,著有《尊攘纪事本末》、《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张裕钊称其“负绝人之姿而有高世之志,于其国及吾中国振古以来治乱得失无不窥;于今日西北以往殊邻绝党、舟车兵械、技巧之制、会盟战功之事无所不究切。慨然将欲有所振于其国者,噤不得施,弢敛奇特,抱独而处”。故为之序,“有取于君之用心,有慨于余之志。”[2](卷一)表明张氏感到冈千仞与自己志趣相投,遭遇亦相似,因而不仅惺惺相惜,还借此作序之机一吐自己的感慨。
张裕钊还感到,中日两国某些文士命运相同,但中日两国的发展趋势和命运则不一样,日本越来越富强,而中国越来越贫弱,危机越来越严重,这是更使他悲观之处。张氏死于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前夕,未及亲见中国被日本打败的惨状,但早在八十年代之初,他就曾以诗《弱水》抒发自己对未来的忧虑:“弱水终难渡,神山不可求,熊螭复隐雾,蛟鳄尽乘秋。来日忧方大,诸公善自谋。独令阊阖上,旰食问共球。”[5](p273)预见中国会有更大的危难。人们或许会责怪张裕钊式的士人过于悲观,但在旧中国,一个更可悲的事实恰恰是:乐观的预言往往成为泡影,而悲观的预计却常常不幸而言中。
二、深沉高穆的文论和诗作
从学术流派而言,张裕钊中年有一段曾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素爱桐城派古文,后来更以高官显位而接过桐城派的旗帜,他一方面肯定桐城派为文章正轨,一方面针对桐城派的规模狭小而纠之以雄奇瑰玮,针对其空疏迂阔而在“义理”、“考据”、“词章”三项内容之外再加上“经济”;又把学习的范围加以扩大,亲自编选《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桐城派创始人之一的姚鼐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的补充读物。桐城派由此号称“中兴”。
但曾门弟子习文,上者仍在韩愈、欧阳修,次者更不出方苞、姚鼐;只有张裕钊假途唐宋八家,而上溯两汉、先秦、晚周,并原本六经,且于许慎、郑玄的训诂,二程、朱熹的义理,均究其微奥。故张氏之文文义精辟,词句古朴峻拔,实际上已脱离桐城派的藩篱而自成一家。曾国藩曾在《求阙斋日记》中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唯张、吴二生,”此即指张裕钊和后来成为清末桐城派代表的吴汝纶。曾氏又称张裕钊的古文“有安石之风,吾既爱之,又畏之”[12](卷四百六十八,文苑三);[13](p119-120)。张舜徽先生说,“盖裕钊与吴汝纶,并以能为古文辞雄于晚清。吴之才健,而裕钊则以意度胜,文章尔雅,训辞深厚,非偶然也。”[14](p528)上述评赞均属确切之论。
张裕钊论文,以“意”为主,而以“词”、“气”、“法”来辅“意”,并又强调一出乎“自然”。他在《答吴挚甫书》中有一段文论曰:“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词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其意与词往往因之而益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词曰气曰法之数者,犹判然自为一事,……唯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动静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词气与法胥从之矣。”[5](p122-123)可知张裕钊之讲求意、词、气、法,已形成其综合的系统的观念,有主有从,而又互相联贯;其最高境界则是浑然自成,渊懿宏肆且不假雕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