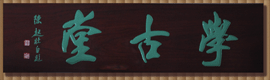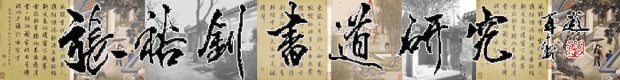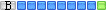张裕钊论《禹贡》三江
丁有国
一、《禹贡》对“三江”的记述
《尚书·禹贡》中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意思是说:三条江水已经导入了大海,震泽(注:太湖,《禹贡》称“震泽”;《尔雅》称“具区”。)也治理得平定了。又说:“嶓冢(山名,在陕西省宁强县北部,漾水源出于此)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又说:“岷山(在四川北部,岷江源于其南)导江,东别(别:另有一条支流)为沱,又东至于澧(在湖南,东流入洞庭湖),过九江,至于东陵(在今黄梅县),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禹贡》对“三江”的记述仅此而已。根据《禹贡》的这些记述,有些问题不易令人明白。第一、“三江既入”,具体的是指哪三条江呢?第二、汉水的水道东流入海为北江,岷江的水道东流入海为中江,则中江必是另一条水道,那么,这条水道从哪里走向呢?第三、汉水与岷江到了江之中下游,实际上已形成了一条水道,又如何分成北江、中江而分别东流入海呢?第四、既有北江、中江,有无南江呢?如果有,那又是哪一条水道呢?这些,都给后人留下了若干疑点。因此,从汉代以来,经学家们解说“三江”的众口不一,其说纷纭。
二、汉代以来一些著名学者对“三江”的解说
最早解说“三江”是东汉班固。班固在他的《汉书·地理志》中首先援引了《禹贡》的记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三条支流),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然后,他解说道:“芜湖,中江出(其)西南,东至阳羡(今江苏宜兴)入海。”又说:“吴,故国,周太伯(周太王长子)所邑。具区泽在西,扬州薮(泽),古文以为震泽。南江在南,东入海”。又说:“石城(今安徽贵池),分江水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过郡二(一、古丹扬郡,治在安徽宣城,辖今安徽长江以南、江苏大茅山以西和浙江天目山西北计17个县;二、古会稽郡,秦置,治在今江苏苏州,汉顺帝时移治绍兴,辖今江苏太湖以东以及浙江的东北部地区的26个县),行千二百。”这些,就是班固对“三江”的解说。
汉代以后的经学家,大都墨守班固的解说,尤其是北魏时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字善长),他在《水经注》中,对班固说的“石城,分江水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构想了一个详细的水道路线图,并且称它为南江。他说:“江水自石城东入为贵口,东径石城县北,……东合东大溪。溪水首受江北,径其县故城东,又北入南江。南江又东,与贵长池水合,水出县南郎山,北流为贵长池。池水又北注入南江。南江又东,径宣城之临城(今安徽青阳县)南,又东合泾水。南江又东,与桐水合。又东经安吴县,号曰安吴溪。又东,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阳山下,径陵阳县西,为旋溪水。”接着又说:“南江之北,即宛陵县(今宣城县)界也。南江又东径宁国县南”。“南江又东经故鄣县(今浙江章吴镇)南、安吉县(今浙江安吉县)北。“南江又东北为长渎历湖口。南江东注入具区(太湖),谓之五湖口”,南江又从太湖出口,经吴县(今苏州)、由拳(浙江嘉兴)、海盐(宁海县境)、余杭、钱唐(杭州)到达余姚,东入海。这是郦道元对南江的详细解说。
按照班固的解说:第一、由毗陵(今常州市)北边东流入海的长江下游是《禹贡》的北江;第二、出自芜湖县(汉代始置,今仍为县,在今芜湖市东南30公里)西南,东流经阳羡(宜兴)入海的水道为中江。他所说的这条水道(中江),实际就是松江。松江的上游段叫荆溪。荆溪是自西向东,经过漂阳、宜兴两县最大的一条水道。但它不出自芜湖县西南,而是由其上源胥溪河,出自与安徽芜湖县相邻的江苏高淳县东北,汇集大茅山以东和苏、浙、皖边境的界岭北坡诸水,东流经漂阳县,又东到宜兴县的大埔附近流入太湖。这就是荆溪,也就是松江的上游段。由太湖出口,东流入海最大的水道也是松江。第三、他所说的“吴,故国,……具区泽在西。南江在南,东入海”,也说的是松江。因为他这里说的“吴”,是在具区泽(太湖)的东边。这就是指古吴县,而不是指古吴国全境。在吴县南东入海的恰恰是松江。可见,班固把南江、中江相混成一条江了。郦道元大概也明白这一点,干脆把班固说的从石城县分江水,东至余姚入海的那条水道称为南江。班固和郦道元对“三江”的解说大同小异,人们称为班、郦之说。
由于班固、郦道元是大家,是权威,所以,许多人在解说“三江”的时候,都牵强附会、左右缝合去附会他们的说法。比如清代学者钱塘(1735-1790),字学渊,号溉亭。此人是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当过江宁府的教授。他是江苏嘉定人,本来就熟悉当地的地形,知道“分江水”的说法不合实际,就拐弯抹角地解释道:“由拳以至余姚诸县,固在吴国之南,是以南江入海于余姚系(关涉)之,又以吴系之。”他的意思是说:从由拳到余姚诸县,都在吴国之南,所以,说到南江入海,就要把余姚和吴关涉进去。附和班郦之说的著名学者还有:姚鼐(1731-1815),字姬传,室名惜抱轩,乾隆年间进士,著名学者,曾任刑部郎中,后主讲江宁、扬州书院四十年,著有《惜抱轩全集》八十八卷,辑有《古文辞类篡》七十五卷,还同孙星衍合编《庐州府志》五十四卷;金蘂中(1735-1801),名榜,字蘂中,乾隆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修撰,著有《海曲拾遗》六卷;孙星衍(1753-1819),字伯渊,号渊如,乾隆年间进士,文学家,曾任翰林院编修,撰辑了《松江府志》等六府县志书;钱学渊(1735-1790),名塘,字学渊,号溉亭,乾隆年间进士,著有《史记之书释疑》等多部著作;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县人,乾隆年间进士,曾任湖广总督、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校刻了《十三经著疏》,汇刻《学海堂经解》一千四百卷。著有《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多种。这些人在各自的著述中,对《禹贡》三江的解说,也都附和班、郦之说。
但是,有些学者认识到班、郦之说中,有明显的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不得不另辟蹊径,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说“三江”。唐代的徐铿等编的《初学记》中引郑康成(郑玄)对“三江”的解释为赣江、岷江、汉江为南江、中江、北江。《国语·越语上》记载伍子胥的话:“吴越之地,三江环之,民无所移矣。”三国时的吴国学者韦昭注释《国语》中的“三江”为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东汉赵晔编的《吴越春秋》解释“三江”为松江、钱塘江、剡江(曹娥江)。晋代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276-324),字景纯。他说:“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庾仲初在《扬都赋注》中则说:“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海,与松江而三也。”这是说:松江东行七十里,分为三条水道,分别流入海,称为“三江”。这一说法,同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中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所说的东江,现在已经堙塞了。
三、张裕钊就《禹贡》三江同吴汝纶的争论
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张裕钊在保定莲池书院以“《禹贡》三江”命题,要学生写作文。他阅完学生的全部文卷,没有一篇让他满意的。于是,他自己写了一篇《<禹贡>三江考》。
四月初十日,他给在冀州当知府的好友吴汝纶写信,其中说:“前月以《禹贡》三江课诸生,颇乏称意者,乃自作一篇,今寄呈。”事隔不久,吴汝纶在回信中指出:对《禹贡》三江的解说,应当遵从班氏志。并且说:“东迤者为南江”,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
闰四月(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八日,张裕钊给吴汝纶的回信中说:“蒙示‘三江当主班志’,所论具有依据,纫佩(《楚辞》“纫秋兰以为佩”,本是“荣美”,此是“赞美”、“赞叹”,之意)无已。至‘东迤者为南江’,阁下以为不易,适乃鄙心之所甚不安者。以此,未敢苟同”。“若欲相与辨论所说之是非,深恐烦劳翰墨,彼此皆为神疲而是非卒不可定。且留此一段公案,俟他日晤见,藉佐谈资”。“想阁下决无降北之理,即不肖亦必不为强敌所屈也。”
吴汝纶看到张裕钊不想打笔墨官司,提出“俟他日晤见,藉佐谈资”,就说张裕钊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因而“外託高言,中实怯懦”。对此,张裕钊在闰四月二十二日的回信中说:“三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