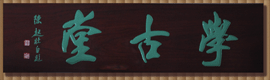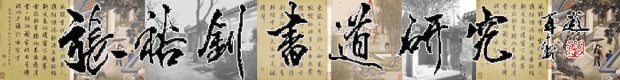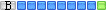略论张裕钊的书法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钟 鸣 天
自从清代中阮元、包世臣提倡北碑以后,在我国书坛上,学习北碑的风气蔚然兴起,使埋没了千多年的北碑书法艺术得以重放光彩,也给清代书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使清代中叶以后的书学艺术为之一振,涌现了不少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但是,在学习北碑中能够陶溶变化,创新发展,独成一格的当推晚清书法家张裕钊。
张裕钊(1823—1894)湖北武昌(今鄂州市)人,字廉卿,号濂亭,道光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先后在江宁钟山书院(凤池书院)、武昌经心书院、保定莲池书院、襄阳鹿门书院任主讲。研究经学训诂、专主音义,善书,工古文,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尝考订国策,著有《左氏贾服注考证》、《今文尚书考证》、《濂亭文钞》等。
张裕钊的书法,熔铸汉魏六朝碑版,创新变化,自成面貌,用笔纯以中锋出之,变魏碑方笔为圆笔,形成内圆外方的独特笔姿,又不失汉魏碑的峻峭风骨,而是更加遒润隽逸。在结构方面,则变魏晋北碑的横扁体势为纵长体势,把魏碑剑拔弩张的刚狠气势,一变而为清矍秀逸之姿。这是个卓越的创造和发展。故深得近代书评家康有为的赞许推崇。康氏在《广艺舟双楫》中说:
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其在国朝,譬之东原之经学,稚威之骈文,定庵之散文,皆特立独出者也。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外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
又说:自隋碑始变疏朗,率更专讲结构,后世承风,古法坏矣,邓完白出,独篆隶,冶六朝而作书。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运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何有宋明,尤为家中兴矣。
康有为崇尚北碑,有意抬出张裕钊来为他“崇碑抑帖论”服务,故对张裕钊的评论,未免有些失实之处。如说张裕钊书法“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就不符合事实。据清末襄阳人钱仲宣《怀旧诗》张廉卿先生条下注云:“曩见先生临池,实自率更入,日有课程,百冗不辍。”而且还有《临皇甫诞碑》墨迹流传至今。从张裕钊的很多楷书墨迹中,亦可以窥见欧书的痕迹。这对康有为“崇魏卑唐”论,是个有力的反击。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当时碑学兴起之后,近百年间还无突出的书家,而张裕钊北碑却有独创性和鲜明的风格,正合康氏的要求,故而用了上面那种不符实际的评论。然而张裕钊书法的成就,还是非常突出的。
近人马宗霍《栖云楼笔谈》说:“廉卿书劲练清拔,信能化北碑为已用,饱墨沈光,精气内敛,自是咸同间一家。”这样评论比较中肯,合乎实际,比较客观。另一位书法大家于右任评论张裕钊书法的诗说:
行笔方圆逼以真,卷头歌诀见精神。
书家自古如名将,一代天生不数人。
对他的外方内圆用笔和笔法歌诀是非常肯定的。把书家的握笔向纸,驱遣点画,譬为名将点兵,是非常形象。特别是“一代天生不数人”这句诗,是髯翁对张裕钊的无上敬佩和景仰。
张裕钊对自己的晚年的书法,也有所评论。他在与吴挚甫(汝纶)的信中谈到:“比来志气衰耗,学殖荒落,日退无疆,无是言者,惟拙书乃颇益长进,独以此沾沾自喜,且自笑。足下闻之,当更为之大笑也。”可见他对自己晚年书法的进益是颇为自许的。下面列举他的几种书法墨迹,以验证他的书法成就:
“向阳野竹先抽笋,待雪官梅欲试花”;
“名将待绘凌烟阁,霄汉常悬捧日心”;
为宫岛大八书枚乘《七发》选段;
行书东坡诗;
临欧阳洵《皇甫诞碑》、《九成宫碑》;
行书《柳子厚墓志铭》、《圣教序》。
从这些代表书迹中,就可以看出张裕钊的功力和独特面貌,是名不虚传的。
张裕钊在书法上的主要成就,是着重实践,在书法理论上研究和发明很少。偶尔在他的著述手稿中,散留下几则有关“永字八法”的新解和用笔、用墨、运腕、运肘等歌诀式的心得体会:
关于永字八法:
一点为侧、二横为勒,四钩为趯、五左为策,六左下为掠,七右上为啄,八右下为磔。
弩如流水下注,磔如巨舰凌波,掠如饥鹰捩影,侧如跃虎蹲崖,啄如利箭破的,勒如长剑抉云,趯如黄蜂出虿,策如潜虬跃渊,折如曲流赴壑,戈如壮士挽强。
关于用笔、用墨、运腕、运肘等:
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入墨涩,发锋远,收锋急,
指腕相应,五指齐力(藏锋深,出锋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