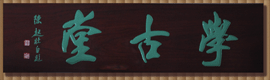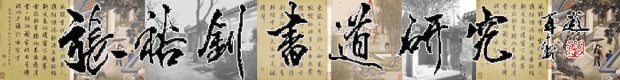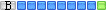论张裕钊《辨司马相如〈封禅文〉》
丁有国
古代帝王,每有封禅之举。所谓封禅,是两项祭祀活动。一是到泰山顶上筑一座土坛,在坛上祭天,叫做“封”;一是在泰山脚下的一座叫“梁甫”的小山上,开辟一块场地,在那里祭地,叫做“禅”。周、秦、汉等朝代的君主,多有封禅活动。
西汉立国九十余年,没有举行封禅活动。至汉武帝刘彻才举行了封禅活动。司马相如写一篇《封禅文》,临死前,嘱咐其夫人卓文君,他死了以后,朝廷会有人来索取他的文章,就把这篇《封禅文》交出去,呈递给汉武帝。
对于这篇《封禅文》,历来的文人都讥笑司马相如,用一个字来概括文章的主旨,那就是“谀”,即对汉武帝阿谀奉承。张裕钊不赞成这种意见。他说:“余以为不然,相如之为此(作这篇文章),正以讽武帝之封禅耳。”他以一个“讽”字来概括文章的本旨。这里,一“谀”一“讽”,意义相反,评价悬殊,谁是谁非,得失之所在究竟在何处呢?按照张裕钊的说法:《封禅文》“无虑(大约)皆诡激傥荡之辞,以谲讽封禅之矫诬”意思是说:《封禅文》大约都是一些委婉偏颇任意而不确切的言辞,用婉言来讽谏封禅的虚妄和反常。我们沿着张先生对这篇文章内容总概括的思路,去分析《封禅文》,便可以得到下列看法。
首先,司马相如用曲笔写周朝无殊异德业,以抑为扬。
《封禅文》中说:“公刘(后稷之曾祖)发迹于西戎(今陕、甘一带),文王改制(改正朔,易服色),爰(于是)周郅(大也)隆,……故轨迹夷(平)易,易遵也;谌(音沈,信也)恩宠洪,易丰(顺承)也;宪度(法度)著明,易则(遵守)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于襁褓(指成王年少即位),而崇冠于二后(文王、武王)。揆(揣度)厥(其)所元(始),终都攸(迅疾)卒,未有殊尤绝迹(奇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蹑(踏)梁甫,登泰山,建显号,施尊名”,“不亦恧(nǜ,惭愧)乎?”
周代果真没有什么“殊尤绝迹可考”,而其踏梁甫,登泰山,建显号,应该感到惭愧吗?根据《史记》的记载:纣王无道,好淫乐,贪女色,唯妲己之言是从。剖比干之心,醢(剁成肉酱)九侯之身,厚赋税以修鹿台,用酷刑而立炮格(音阁),造酒池,悬肉林,百姓怨望,诸侯叛离。当此时,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往归。当武王起兵伐纣时,诸侯不约而赴者八百,与纣兵战于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大败纣兵,纣王逃到鹿台,纵火自焚。武王灭商,后二年即死。成王年少登基,由周公理政。周公勤于国事,为了接待士臣,他一饭三吐哺(吃在口里的食物,来不及嚼细吞下去,只好吐出来),一沐三握发(洗一次头,有时多次停下来,握着头发去接待前来言事的人)。在《康诰》中,他主张“明德慎罚”;在《酒诰》中,他劝戒士臣们珍惜粮食,勿湎于酒;在《洛诰》中,他告戒士臣们要满足天下士民的愿望和要求,树立周邦的诚信和榜样。这时,各国诸侯对周王朝的政令,“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七年之后,周公还政给成王,自己又回到群臣之列。孔子对周公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一直希望能够像周公那样辅佐一个国君,成就一番事业。他到晚年还叹息道:“甚矣吾衰也,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意思是说:我衰老得太很了,再不能像周公那样干一番事业,梦想破灭了啊!孔子和孟子对周代的评价都很高。孔子说:“周之德,其可谓至(最高尚的)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又说:“周监(通鉴,借鉴)于二代(夏、商),郁郁乎(丰美淳厚的样子)文哉(文明呀)!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说:“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他又引《尚书》中的话说:“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句意是说:伟大光明呀,文王的谋略!伟大的继承者呀,武王的功烈!
周代的功业如此伟大,道德如此光辉,而司马相如说它没有什么“殊尤绝迹可考”,对于搞封禅活动应该感到惭愧,这说的是反话,用的是曲笔,其用意是要说明:没有什么德业的人,就不应该举行封禅活动。这一点,张裕钊是非常理解的,所以,他说司马相如的《封禅文》“皆诡激傥荡之辞”。这个断语是非常恰当的。
第二,用夸饰的笔法来渲染大汉之德,寓褒于贬。
司马相如在《封禅文》中说:“大汉之德,逢涌原泉(逢,通烽,如烽火升涌,源泉奔流),氵勿氵矞(mìyù)漫衍(流动散布),磅礴四塞,云布雾散;上畅九垓(九天高处),下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