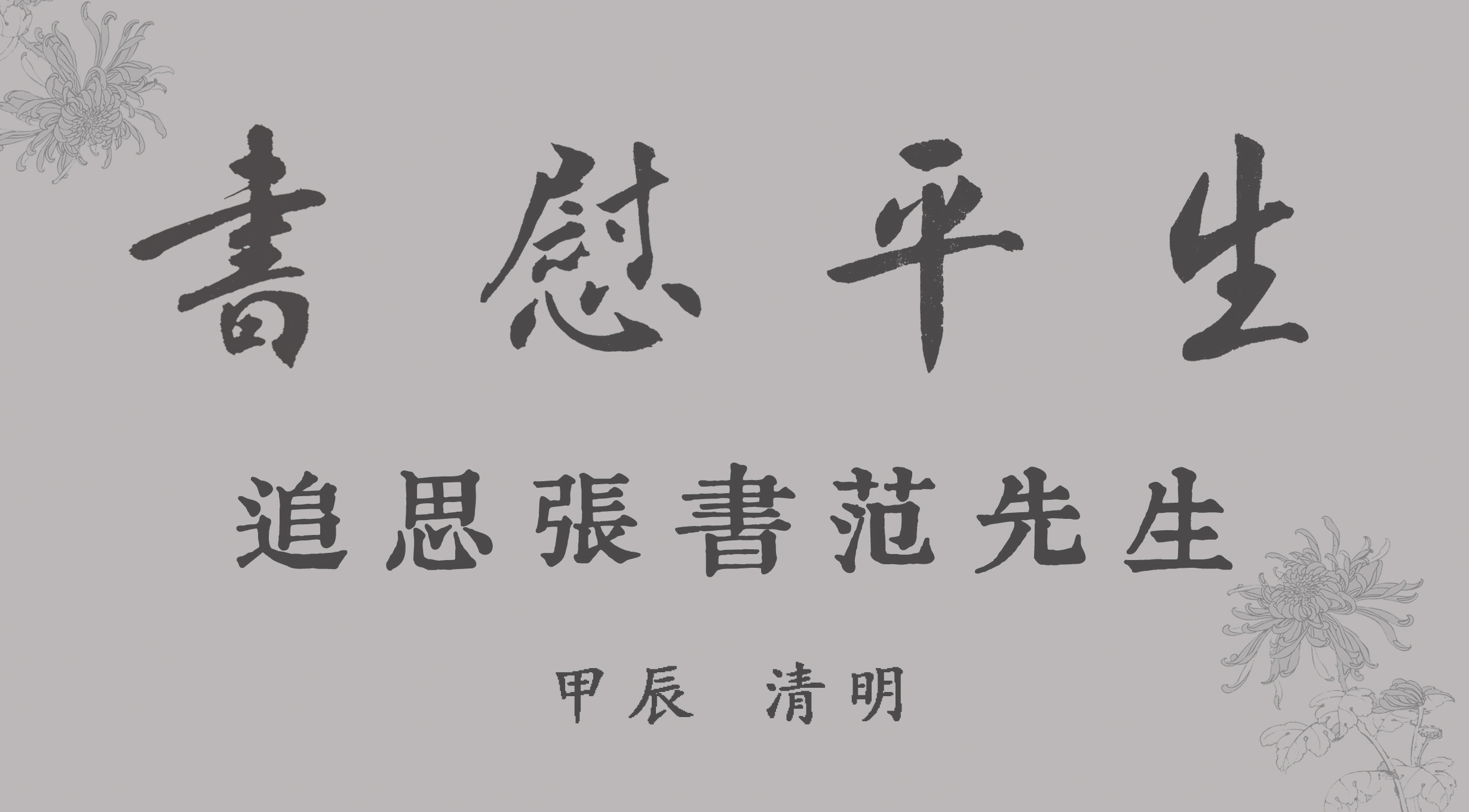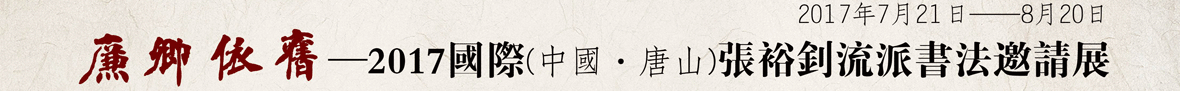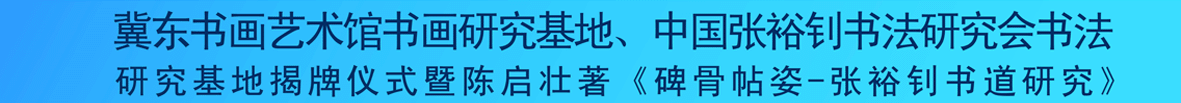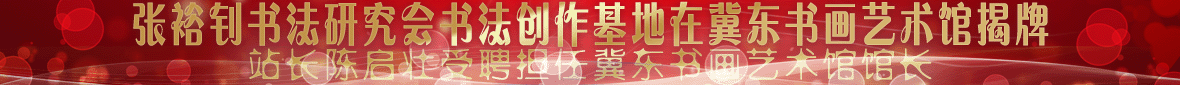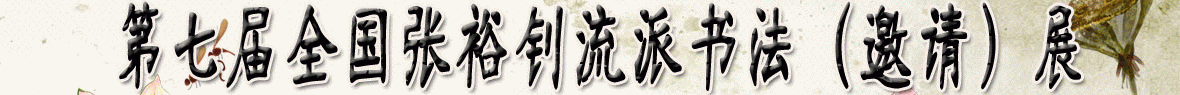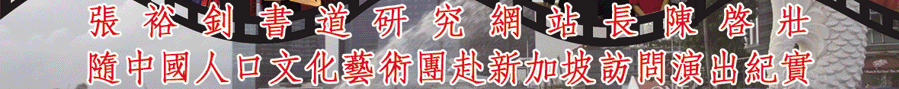联墨相晖多古意 亭林掩映见天机
一一略谈张裕钊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其书法艺术
陈启壮
作为晚清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和大书法家,张裕钊的学养和功力是极其深厚的,其书法更是以古为新,熔铸百家,创出世所共称的“张体”书法,被康有为誉为“集碑之大成者”.笔者通过对张裕钊及其书法艺术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发现,张裕钊先生深厚的哲学修养和独特的美学思想及文人品质,支撑了其独创“张体”书法的理论基础。笔者试着从其整体风格以及具体笔法、结构、章法等诸方面加以分析:
张裕钊先生书法在整体风格上力主气韵为先,推崇神采意趣,天骨奇崛,尊古为新。所作以魏碑为根基,复参以帖法,结体平正之中见欹侧,用笔劲健之中见婀娜,翻转提按,沉雄浑厚,刚而不烈,秀而不媚,外方内圆,避熟就生,墨彩焕发,体现出强烈的艺术个性。张公作为著名学者,学养深厚,对哲学亦多有参悟。他深知世界万物相反相成,按阴阳规律体现大自然,这包含了书法笔力的刚柔,笔画的粗细,结构的上下左右,向背顾盼,行笔的阴柔阳刚向自然万物取象。张裕钊先生在襄阳与友人谈书法时就曾说到“不通阴阳造化者,不可与言书法,此即画家阴阳向背之理”。正是因为深知此理,张公才由帖转碑,再由帖养碑,碑帖相融,矛盾而统一。他更知只有溯本求源,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对传统参悟得越深,其中三昧必心知肚明,去粗取精,才能多所创获。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张公学书的道路上,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他通过对古人大量书法佳作“未尝一日辍”的研习和参悟,找到了书法艺术领域共性的规律,再从共性之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个性。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过程是何等艰难,因为他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是张裕钊却让人不可思议的做到了,而且“众里寻他”的结果是十分成功的。这种以古为新、古中求新的美学思想是那么辨证而富有哲学意味。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审视大量张公书法作品时,便会发现张氏对传统的参悟力有多深,众多古贤的影子会立刻浮现于前,而其独特的“张体”特征又是那么富有创新精神,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熔铸百家的本领又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值得一提的是:时人论及张裕钊先生书法,很少提及他与书圣王羲之
的关系,而笔者在近期学习张氏论学手札作品后,随意又写了一段时间书圣的行草书信,竟发现张公论学手札行笔之节奏韵味与书圣的书信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不由使我想起以前见的张氏临写的兰亭序等书圣作品,足可见张裕钊先生对晋人尚韵的深刻理解,这也证实了张体书法力主气韵为先,推崇神采意趣的传统根源.这种内美的修炼需要具有极高的眼力和超众的才华,而张裕钊先生的才华和眼力恰恰来自于他那极其令人尊崇的文人品质。
张裕钊先生书法的风格是和谐统一的,但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体到其笔法、结构及章法层面上,他的哲学和审美思想也更具体,更深刻,更见高妙。凡是研习张裕钊先生书法者均知其笔法独特,与众不同。笔法又分为执笔和运笔。就执笔而言,写张体书法尤讲沉肩坠肘,指实掌虚,拇指与食指从不同方向向下施加的力要与中指和无名指等向上施加的力相等才能使笔管保持平衡,这样写起字来才更得心应手。而运笔对于写张体书法来说更为重要。首先,张体书法强调“中锋行笔”。张裕钊先生曾谓“汉人用笔,莫不中锋,其法至唐代尚能保存,宋代以后,则失传古法,高浑遒劲之书则少见矣”。那么,更进一步讲,中锋从何而来,又如何表现呢?张裕钊很高明,他“隶于汉,篆于秦”,尽得古法之秘。众所周知,习篆书首重中锋运笔,因笔画圆转流畅皆来自中锋。而隶书在保证中锋的基础上,用笔更加丰富多彩,克服了篆法的单一运笔。这里就涉及到了具体运笔技法一捻转笔管和重按轻提。因为毛笔的笔锋是软的,线条的方向在运笔书写过程中是不同的,这就要求通过捻转笔管将笔锋调整为中锋行笔,同时还要求通过重按轻提来保证写出的笔画既得中锋,又骨力内涵,气韵生动。这里需注意两点:一。捻转笔管的目的是为了调成中锋,因此要适度、灵活,不可机械的夸大运用。尽管有记载说张裕钊经常备一牙管练习捻笔,但我们也应知道他仅仅是为了让手指更加灵活自如而已。也就是说,捻转笔管仅是运笔的方法,中锋才是目的。二.重按轻提的技巧强调”稳、准、狠”三字,是指在书写过程中干净利索的落笔和行笔,节奏感要强烈,要充分体现动与静、快与慢、虚与实的矛盾统一关系,而并非仅指笔画的粗细和大小等。日本宫岛咏士作为张裕钊先生的亲传弟子曾经写道“书道之要,首在捻笔,劲直之基,在第四指,微妙之作用,存于拇指尖,来锋远,收锋急,姿势则得。汉唐人用笔,悉由中锋,宋则亡,千有余载,廉公独悟,可谓神矣”。这段话形象地描述了张体书法笔法中方圆兼备,中侧并用,外方内圆,曲直相间,动静结合等诸多哲学、美学观点。 .
张裕钊先生书法的结体特征是中宫紧密,外画开张,上紧下松,以折代横,平中见险,体势方正而笔画圆浑。他不仅保留了早期写帖时欧阳询的险峭和褚遂良的流美以及颜、柳的大度雍容,更汲取了龙藏寺的宽博,北碑的率真等结体特征。尤其是张氏在中晚年作品中十分留意阴阳向背,这点无论是从其楷书代表作品《南宫碑》中,还是他的大字对联作品都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张氏这种汲取各家之长,以辨证为美、以中和为美的思想显然是非常睿智和高妙的。这里需强调:张裕钊书法外方内圆的个性特征十分鲜明,但这种外方内圆除了在某些笔画如“钩”“折”处需着意外,更指其用笔多呈圆势而体势多方的特点.另外,在实际书写过程中这种特征不能过分夸张,不能过方过圆,要能方中有圆,圆中有方,亦方亦圆才到好处,而美的容量才会更大。
张裕钊先生对书法章法亦颇为讲究,每创作一幅作品,均由内容定形式。我们既能看到张公所书的沉雄浑厚、气势宏伟的大宇作品,如《宝剑赞》、《崔瑗座右铭》及多种对联,也能看到其所书的极具阴柔之美的作品,如张氏为宮岛咏士所书的横幅长卷《客曰八月》作品。同时张公既能写以静为主的极其工整的楷书作品如《南宫碑》,又能写以动为主颇为自然高妙的行、草作品,如《论学手札》。张公对中堂、条幅、对联、长卷、扇面、册页等各种章法幅式均有杰作传世。当然,更让人赞叹不已的是,张裕钊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功力,非常巧妙的解决了其书法风格的变化与统一问题。无论作品雄与秀,静与动,各种章法幅式均体现出了独特而强烈的张体书法风貌。仅这一点,张裕钊先生就颇具大师风范。尽管其书法也存在结体宽博、平易及松散之病,因政治及历史原因还颇受冷落,但这丝毫不能掩饰他的伟大和崇高。近些年来,研习张公书法者曰益众多充分证明了其书法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
笔者从整体风格和具体笔法、结构、章法上,对张裕钊先生书法中所折射出的深厚哲学修养和睿智高妙的美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虽为一孔之见,不免失之于偏,却也是亲身体会实践之言。张裕钊先生在书法艺术领域处处制造矛盾,随即用高超的本领解决矛盾,不断地否定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凡事必贵其难”,张公这种“履险如夷,因难见巧”的本领,正是其书法难能可贵之处。可以说,张裕钊先生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在他的书法艺术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甚至贯穿于他的整个艺术人生。也正是由于张裕钊先生这种深厚的哲学修养,决定了他的美学思想的个性化,更决定了“张体”书法艺术的鲜明个性特征,从而指引他用了一生时间独创了“张体”书法流派。这对于我们后人的启发意义是巨大的。笔者不才,愿为继承和宏扬“张体”书法流派身体力行,为明心迹,曾自作论“张公书法”绝句一首,恭请诸位专家指正:“慧眼独观畏硕儒,南宫宝剑辟途殊,寒梅覆雪藏青骨,卓尔不群数点朱”。
2003年.6.8于河北唐山“学古堂”书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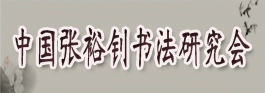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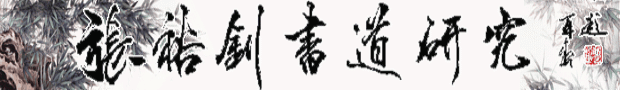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