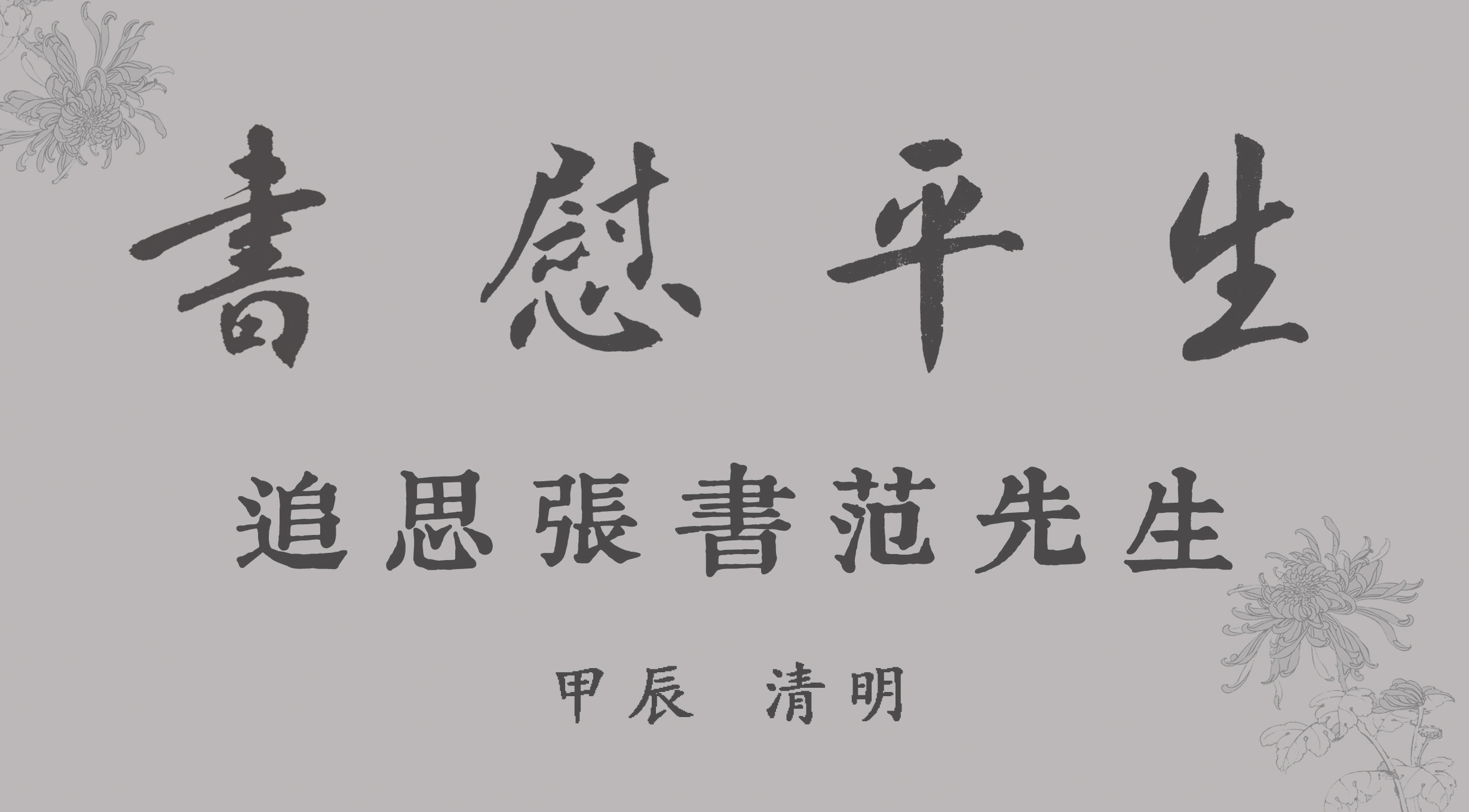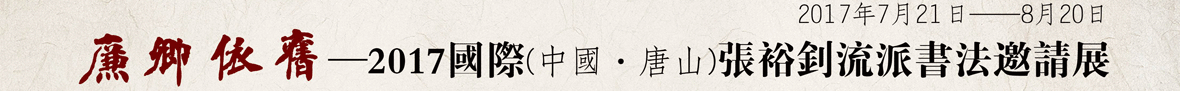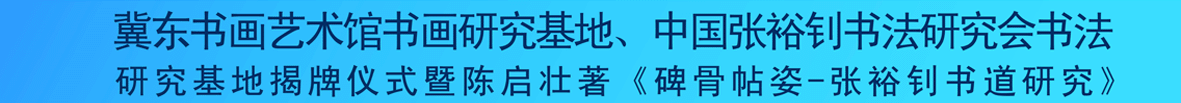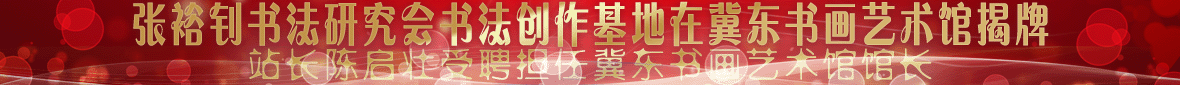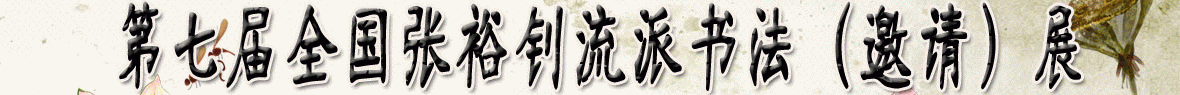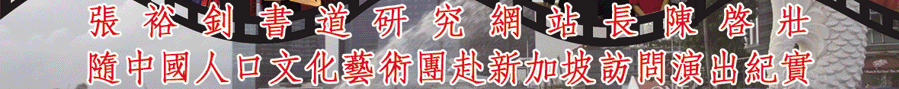张裕钊的时局关怀及文学特色
罗福惠
清末以古文辞雄于文坛、被视为桐城——湘乡派后劲的张裕钊,其实并非仅是文辞之士,他关注时局,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而且他也很早就摆脱了桐城派的拘束,形成了自己思想和文学的独特风格。
一、忧患与憧憬交织的时局关怀
张裕钊(1823—894)字廉卿,武昌(今鄂州市)人,晚清著名
文学家、学者兼书法家。少年读书时即鄙弃八股制艺,好读宋人曾巩的《南丰集》。咸丰元年(1851)中举,四年后考国子监学正,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阅卷赞赏其文,授予《文选》,并说“徒摹唐宋文而不及《文选》,则训诂弗确,不能几于古”。张裕钊进而致力于《史记》及前后《汉书》,尤服膺司马迁,称其“善记言,简略毕中,不亚《左》《国》,班、范非其伦。而班、范擅长词赋故其论赞叙述之言率警练;范则排比为齐梁先驱,要皆文章之宗也”。可知张氏学古文,不拘一家,能得诸宗之长。
张裕钊其后曾入曾国藩幕,学术上直接受曾氏指点.与黎庶
昌、吴汝纶、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曾国藩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而身居高位,其幕僚门人亦多得通显,只有张裕钊虽相从十数年,独以治文教学为事。他不热心政务,故离开曾幕和退出仕途甚早,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起,曾先后在武昌勺庭书院、江宁风池书院、河北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樊鹿门书院主讲席三十余年。门生满天下,较著名者有江苏学者范当世、朱铭盘、状元实业家张謇、湖北金石学家刘心源、日本学者宫岛咏士等。其治学则考订《国语》、《国策》,著《左氏贾服注考证》、《今文尚书考证》,文章则集中在《濂亭文集》,该书为其门人海宁查燕绪所刊,刻印精美,收录文章八十五篇,诗二卷。
从张裕钊有关文章的内容来看,在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危局以
及解救中国的方法等问题上,他的思想颇近于洋务派。他说:“自
泰西人创兴轮舟,驰骤大瀛海之上,上天下地,日星所烛,霜露所濡,穷幽极遐,靡不洞辟。我国家长驾远抚柔服,焘冒交通市易.申结盟约者殆数十国”,“危机衅端伏见不常”,“镇抚捍御.艰危万途”。意思是说由于西方持其先进科技和武器,把势力扩张至世界各地,中国不可避免被卷人其中,从而产生各种矛盾纠葛,中国人因此看到了许多新奇事物,但中国也就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和危机。张氏这种“世界观”和时局观应说是比较全面而深亥的。但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士人,仍有放不下架子、掩饰屈辱失败的心态,于是把西方的东侵说成“自国家怀柔包荒,日月照临,天所覆焘,莫不来宾。海外奇技异物、火器轮舟,诸瑰新似诡骇怪,旷古不睹之事,并交于中国”。对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并无多少谴责,突出的感受是奇、异、诡、怪;同时把中国的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等等,说成是“驾远抚柔”、“交通市易”和“申结盟约”。显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到当时朝廷和官场习用语言和表达方式的影响,用自欺欺人的字眼掩饰中国的失败;另一方面在光绪十年(1884)以前的洋务运动前期阶段,所谓同(治)光(绪)中兴的假象还没有打破,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还未暴露出来,故张裕钊多少还有一些乐观和幻想。
同样,张氏此时还有一些类似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以为“天
地之道.日新而不已,则文明亦日辟而莫知所穷”。他所谓文明曰辟,既包括西方科技器物等文明的东来,还尤其自信中国的“周孔蔽之,曰得人而已。”张氏没有看到.自强或曰洋务运动最根本的不足,是没有触动落后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而视其失误首先在于未注意到人的问題,可说还未能切中根本,但他能看出当时重物不重人的弊病,也仍可算是卓识。
张裕钊关于“得人”的思想,可分为待人、才人、育人三个层次,可说还是较为全面的,不过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他都明显受到曾国藩父子的影响。在待人求才上,张氏认为在高位者必须象当年曾国藩那样的“名德重臣”。“既夙负知人之量,又益慕想殊,尤虚伫贤哲,早夜旁求,皇皇若不及”,才能得到人才,而且所得甚多,“九州之大,必有魁桀之士起而应之者”,“豪俊响应,焱合景从”。只要有了众多人才,就能“举议者之所云,次第而布之,一皆确然收其实效”。
怎样的人才算人才?或者说当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张氏
认为,象曾纪泽这样的人才应该是人们的榜样,他说曾纪泽“博极群籍,洞晓古今治乱得失之故,益讲求时务,无所不究切。尤以疆事孔殷所系,乃绝艰大故,于彼我强弱短长之数、语言文字学术异同、舟舆器械良苦利钝、财贿生殖,万货百昌,赢诎盛衰,皆博考深思而心知其故。……干品万汇,宏巨密微,默识洞贯,总八极而内于寸心。故自朝野上下,无远迩、无愚智贵贱,莫不以为洞明时务未有及侍郎者也”。曾纪泽是曾国藩长子,幼时接受系统传统教育;及长,受其父办洋务的影响薰陶,学习西方各种知识,又在国外八年,因而学贯中西,对中国和世界均有深切了解。1880年他40岁时,曾与沙俄谈判,改订昏庸误国的崇厚与俄国订立的条约,经反复折冲,使中国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仅有的少数几次成功的外交谈判之一。四年后中法战争爆发,他又“与法人辩争,始终不挠”,确实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干材。张裕钊以曾纪泽为当时中国亟需人才的范例,说明他的人才标准是进步的、也是讲求实际的。
在育才问题上,张裕钊曾集中论及两点。其一是批评当时的
教育制度和方法.他说,“唯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
但当时“彼所以造而成其才者失其道”,仅“学为科举之文而已”。
清代的中等教学设施有两种,一是州县所设学宫,属官办性质,由教官主持;一是书院,屑半官方或民间性质,由山长主持。清中叶以来,“郡县之学官权位轻而职业废,不足以鼓舞振起天下之才,于是士之有意进取者常相率聚于书院。然书院之所课其科举之业也,其主此者亦皆以科举之业进者也”。这就是说,当时的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是遭人轻视的末等官,由于位卑权微,这些人并不尽心尽责,因而州县学宫形同虚设,倒是书院能吸收一些学子。但无论是学宫还是书院,都是把教八股文、应付科举考试放在首位,学子也大多致力如此,目的是顺着科举之路,由秀才、举人、进士一级一级爬上去,好出仕做官,故“相习而靡者,苟得之弊中于人心,而莫有能拔乎其间者也”。除了教学八股制艺之外,士人所习.“或专意于考证词章之末而遗其本,或空谈性命而时不免于固陋。”到了近代,“海内兵起,人益废学,而俗曰以敝。士之通知古今而可以为国家之用者,盖往往数百里而不得一人也。”总之是积弊深重,人才奇缺。 其二是批评当时社会风气败坏,人人竞逐私利,而能满足其利欲的最好途径就只有作官。张氏指出,当时作为人子.能使父母高兴的是富贵利达;父母所希望于儿子的也是富贵利达;丈夫萌庇妻子的、妻子仰仗丈夫的,也仍然是富贵利达。“士大夫一沉于室家之累。身之不显则内愧妻子,而若不可为人;为子者亦若唯是可以奉承其亲.非是则危不可以为子。悉家人父子恤乎唯一官之得失为愉戚。……夫俗之日坏.而人才之所以不振,职是故而已。”然而这些人表面上却道貌岸然,“其人能瞠目攘臂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而已”。所以张氏忍不住满腹忧虑地问道,“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又安、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厂
针对当时教育制度窳败、士人不学和学无实用,且一心当官求私利的状况,张裕钊利用教学和著书等各种机会,设法挽救。他强调,“一介之士皆与有天下之责焉。将欲通知古今,讲求经世之大法,稽诸古而不悖,施之今而可行。其必自读书始矣。”然而中国之书多至汗牛充栋,读书亦“有考古之学,有知今之学,……二者固相须为用,然果孰在所缓、孰在所急”?即如考古之学一道,又有“小学”、“金石”、“史事”,“又其外杂史传记谱录之属,殆不可数。学者童而习之,白首而不能究,……其无乃鹜其近小而不急者,而转遗其大者远者欤?”话讲得很全面、很委婉,考古之学、知今之学都无遗漏,但其更重视知今之学,认为读书须注重大者远者的倾向十分明显。他曾反复强调,“古今时势异宜,锲舟求剑,胶柱鼓瑟。适足以乱天下。”尤其是当时的生存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战争,所以他虽然批评洋务运动有专讲练兵制器、购船筑垒的片面性.但也承认“自古内外强弱之势,一视兵为轻重”。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张氏力图纠正拘守故常、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的努力。 对于社会上人们争趋私利的风气,张氏也力图挽救。他认为,对此首先要引导和鼓励读书人立定崇高志向,再通过他们来影响社会,“士莫先于尚志。而风俗之转移,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今天下师儒学子,诚得一有志之士,悯俗之可恫,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由一人达之一邑,由一邑达之天下”,颓风未必不可挽,社会环境未必不可改变。
张裕钊因早年辞官,一直致力于著述和教学.不大直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故后之研究者多以其为有艺术性成就的文人,甚至有人批评他脱离实际。其实并不尽如此。他曾说,“道不足而强言.虽振厉其气,雕绘其词,而座无以餍乎人人之心。深造道德而自得于其心,则凡所言而莫非至道之所寓。”就是说,没有思想深度而故作大言,人们不会理睬;有了真知灼见,随时随事随意为言.都能包含有用的道理。《濂亭文集》的首篇《辨司马相如封禅文》.其实就是该书的“文眼”。在这篇文章中,张裕钊力辨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不是向汉武帝献谀,而是“正以讽武帝之封禅”,“其辞隐”而“刺讥深至”。并称司马相如等人的文章“其用意皆至深远难识,无苟为之者也。以其难识,世乃徒观其外而议之耳。”同样,张的文章也多是意思深远而隐晦,少有激烈的言辞和直截了当的批判,但其关切社会问题的深心、其顺应时代需要而提出有关改革建议,都斑斑可考。
但张裕钊不仅文思深沉,而且思想悲观。他深知当时颓势难挽,而自己的才学和主张亦难见用,故常借他人之酒以浇自己胸中垒块。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号鹿门)曾慕张氏之名,来保定莲池书院相访,并为其书《藏名山房文钞》求序.冈千仞与王韬亦相知,著有《尊攘纪事本末》、《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张裕钊称其“负绝人之姿而有高世之志,于其国及吾中国振古以来治乱得失无不窥;于今日西北以往殊邻绝党、舟车兵械、技巧之制、会盟战功之事无所不究切。慨然将欲有所振于其国者,噤不得施,韬敛奇特,抱独而处”。故为之序。“有取于君之用心,有慨于余之志。”表明张氏感到冈千仞与自己志趣相投,遭遇亦相似,因而不仅惺惺相措,还借此作序之机一吐自己的感慨。
张裕钊还感到.中日两国某些文士命运相同.但中日两国的发展趋势和命运则不一样,日本越来越富强,而中国越来越贫弱,危机越来越严重,这是更使他悲观之处。张氏死于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前夕,未及亲见中国被日本打败的惨状,但早在八十年代之初,他就曾以诗《弱水》抒发自己对未来的忧虑:“弱水终难渡,神山不可求,熊螭复隐雾,蛟鳄尽乘秋。来日忧方大,诸公善自谋。独令阊阖上,旰食问共球。”预见中国会有更大的危难。人们或许会责怪张裕钊式的士人过于悲观。但在旧中国,一个更可悲的事实恰恰是:乐观的预言往往成为泡影,而悲观的预计却常常不幸而言中。
二、深沉高穆的文论和诗作
从学术流派而言,张裕钊中年有一段曾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素爱桐城派古文.后来更以高官显位而接过桐城派的旗帜.他一方面肯定桐城派为文章正轨,一方面针对桐城派的规模狭小而纠之以雄奇瑰玮.针对其空疏迂阔而在“义理”、“考据”、“词章”三项内容之外再加上“经济”;又把学习的范围加以扩大,亲自编选《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桐城派创始人之一的姚鼐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的补充读物。桐城派由此号称”中兴”。 但曾门弟子习文,上者仍在韩愈、欧阳修,次者更不出方苞、姚鼐;只有张裕钊假途唐宋八家,而上溯两汉、先秦、晚周,并原本六经,且于许慎、郑玄的训诂.二程、朱熹的义理,均究其微奧。故张氏之文文义精辟,词句古朴峻拔,实际上已脱离桐城派的藩篱而自成一家。曾国藩曾在<求阙斋日记>中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唯张、吴二生,”此即指张裕钊和后来成为清末桐城派代表的吴汝纶。曾氏又称张裕钊的古文“有安石之风,吾既爱之,又畏之”。张舜徽先生说,“盖裕钊与吴汝纶,并以能为古文辞雄于晚清。吴之才健,而裕钊则以意度胜,文章尔雅,训辞深厚,非偶然也。”上述评赞均属确切之论。
张裕钊论文,以“意”为主,而以“词”、“气”、“法”来辅“意”,并又强调一出乎“自然”。他在《答吴挚甫书》中有一段文论曰:“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词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其意与词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词曰气曰法之数者,犹判然自为一事,……唯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动静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词气与法胥从之矣。”可知张裕钊之讲求意、词、气、法,已形成其综合的系统的观念,有主有从,而又互相联贯;其最高境界则是浑然自成.渊懿宏肆且不假雕饰。
张裕钊所谓“意”具体是些什么?综观其所论及,归纳起来有两点是最主要的,一是“中和”.这是他“原本六经”的反映.“六经著天下万事万理,不可纪极,要其归则中和二言足以蔽之矣”。所以他的文章深沉意隐,思想不疾不徐,不顽固守旧;亦无激烈的批判斗争精神。二是“利泽天下”,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他在给弟子范当世写的文章中.曾以“云”作比喻,把文章的气势、变化和功用形象地表现出来.称文章要如大自然中的云,“?翁然起于山川之间”,“弥漫潢洋旁魄于大地,及其上于天也,鸿洞缜纷,……倏忽万变”,“至其施利泽于天下也,……其积也厚,其出也不穷。”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颇值得为文者体味。
张裕钊亦善诗,所作多为五言和七言,题材比较广泛,但绝大多数为抒发怀抱之作。在思想内容上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淡薄名利而又多怀幽愤,早年多为个人怀才不遇而感慨.晚年则更多为国势倾颓而忧惧。如《端居》云:“我生固坦荡,畏从簪绂俦,多仪困缠缚,貌语强咿嗄。……古来贤达人,往往沈林邱,跌荡从野老,傥遇东陵侯。”该诗作于金陵(南京).当时他在曾国藩幕中,眼看官场的繁文缛节、装腔作势,他就十分反感和头疼,因此不乐于与其为伍,以其坦荡的个性,宁愿作闲云野鹤一样的散人。《戊寅新岁口占》云:“群公玉珮趋青琐,九市华灯缀绛绳,休怪先生浑不出.年来心绪冷如冰。”其落落寡合的心情和行动均不适于官场,大约这也是他很早就退出仕途的原因之一。但当真正放弃仕途进取之望、不与禄蠹交往之后,他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如(秋夜}云:“壮怀早读范滂传,晚学今耽小戴经,犹有忧时心未灭,步檐遥看上台星。”《甲戌登高有感》则云:“兴亡历历阅千年,眼底青青六代山,南北推移随世重,安危盘错惜才难。”摆脱得了龌龊官场.却无法挣脱复杂危殆的时局。他深感需要人才出而救世,而人才却是既少且难被任用.忧愤至极时,对自己倾毕生精力而学文为文,也觉得没有丝毫意义和价值。如《戊寅偶书》感叹:“少日苦求言语工,九天九地极溟鸿,岂知无限精奇境,尽在萧疏黯淡中。”不独自己如此,古时大名鼎鼎的韩愈又何能例外?《古诗之一》云:“退之勇卫道,自以时无比,攜文追卿云,著书排二氏。饥寒忽相迫,曩怀挫复几,文章小技耳,何其太自喜。”就是说,自己范范以求的文学境界,有时竟觉得虚无缥缈、没有多大意思了。至于文章的作用更不过就是那么回事,象韩愈那样勇于卫道和自负,但连个人的生计都解决不了,其壮怀又能坚持多久呢7
中法战争开始,张裕钊已进入老年,他对个人的出处显隐已不太介意了,但由于自强运动的失败和国势的更趋危急,其忧愤也更加深重,而且多为国事而发。如《孤愤》云;“议和议战国如狂,目论纷纷实可伤,万事总为浮伪败,一言无过得人强。尽焚刍狗收真效,宁要束蠡列众芳。独把罪言倚枕读,一声白雁泪千行。”认为中国之败仍在虚应故事.办事缺乏实效。由于自己没有实力,故无论和战均无法摆脱危局。不久清政府接受屈辱条件,与法国订立和约,他更感慨万端,《罪言》称“……岂有疗饥餐毒药,可怜从瞽问迷途。噬脐它日宁堪说,十万横磨一掷输。”批评清政府只顾目前,听信妥协投降主张,轻易把中国将士的战斗成果断送,因而必然招致更多的欺凌。
张裕钊在世的最后一年,已是甲午中日之战前夕,他已经彻底失望,《冬螟》云:……贪污成俗国维破,砥柱无人士气孤。世事久经归袖手.年除聊复醉屠苏。”其绝笔《眼底》吟道:“眼底喧嚣实可怜,江河日下作深渊。纷纷燕雀何足数,采釆浮游空自鲜.冀北名驹谁万里,辽东归鹤已千年。散人岂合知时事,独念皇家一怆然。”小人得志,颐指气使;志士灰心,酒歌当哭。中国面临更大的灾难,但在灾难到来之前,张裕钊首先想到的是“皇家”,这说明张裕钊式的传统士人,忠君观念已压倒一切。其实,当时危局的根源,正在“皇家”已完全成为国家、社会、人民群众的对立物。要救中国和解除人民的灾难,首先就应该推翻“皇家”,但张裕钊见不及此,所以其思想不够先进。
张裕钊诗歌内容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中国古代圣贤流露出怀
疑。本来在他的文章中,就极少对圣贤的顶礼膜拜,不过还没有直接的质疑和嘲笑;但在诗歌中,一方面可能是直抒胸臆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到阮籍、陶渊明、李白、陆游的影响,故对昔之圣贤颇多不恭的倾向。如《夜》表示“圣贤去我已千载,手把遗编阖且开。唯有多情天上月.苍茫曾照古人来。”再如《丙子春感》云“酣歌痛饮从疏放,跖矫孔颜谁是非”;《雪夜课经图为方生宝彝题》则云:“所贵俊杰识时务,今日岂复古初侔?尧舜糠秕竞何物,枉持万卷输兜鏊。”虽然这些话不可视作庄重之语,或者竟是酒话和愤激之词,但再联系他写下的诸如《对酒》“千龄百代一山邱,新人旧人莽相续。饥饱苦乐度一世,若为太仓赢粒粟”;《留别莲池书院诸生》慨叹“人生天地间,有若桴浮海,波涛一冲击,谁能知定在?”等等为数颇多的感叹人生之作,就可知道他对圣贤的不敬慕也是真情流露。因为圣贤都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一个极度悲观失望的人很难从内心崇拜圣贤。这种现象也体现了当时士人的双重性格,他们在写文章和教训人鼓励人等庄重场合,力求不违离圣贤之道;而在流露真情时又往往对神圣的东西表示怀疑乃至亵渎。
张裕钊酷爱书法,由魏晋六朝之书法而上窥汉隶,通过数十年的揣摩钻研.尽得汉魏人用笔真谛,并融合北碑的高浑、唐碑的整肃而自成一家。他以为“汉人用行,莫不中锋,此法至唐代尚能保存。宋代以后,则古法失传,多用偏锋,高沉遒劲的字就少见了。”清末刘熙载、钱葆青诸人都高度评价张氏的书法,尤其是康有为,更称赞“其书法高古深穆。点画转斩,皆绝痕迹而得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人得意处,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由于康有为的誉扬,张氏的书法一度在国内很有影响。
张裕钊的文章和书法还驰名日本。除前述他与冈千仞(鹿
门)的文章酬答、诗歌唱和之外,他与宫岛父子的交往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原来黎庶昌出使日本时,张氏长子张沆作为随员同行,在日本结识宫岛栗香(诚一郎)、宫岛彦(咏士)父子,宫岛彦遂在他二十岁时来到中国,整整七年时间一直追随张裕钊学习汉文和书法,师生情同父子。直到张裕钊去世后,宫岛彦才回日本,创立善邻书院,教授汉文和书法。宫岛既得张氏书法真传,而张氏书法在日本通过宫岛的弘扬传播,已俨然成为一大流派。善邻书院至今犹在,前任院长是宫岛彦之孙宫岛吉亮,他曾在1984、1985年两次组织书法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北京和武汉举办“张裕钊、宫岛咏士书法联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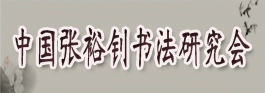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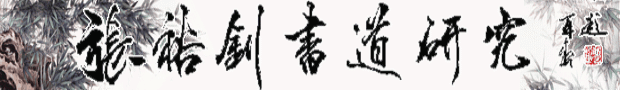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